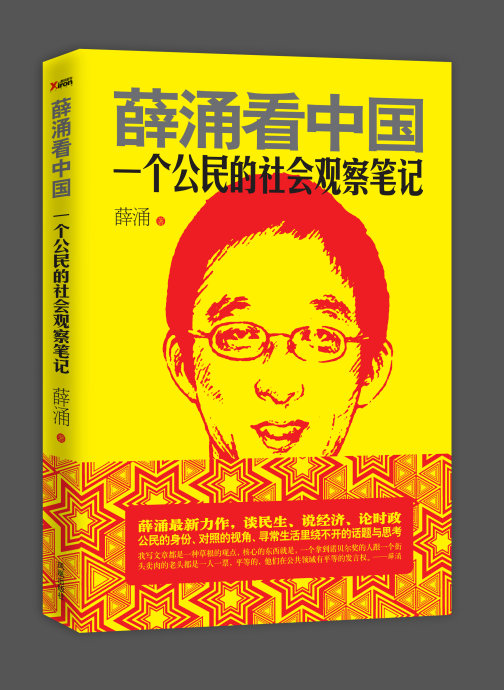
答《華商報》記者問
他自稱是一位“反智書生”,但其智慧的目光,每每掠過遼闊的太平洋面,注視著這個正上演著諸多精彩故事的故國,思索并發言,且常常引起熱議,成為社會上的一時焦點。他認為中國在走向大國的途程之中,要舉全社會之力,讓大家都能夠“高高興興做大國”,而不是“國富民窮”或“大國小民”,他,就是在時評界聲名日隆的學者薛涌。8日,薛涌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1坦誠論大國
“負責”就要擺脫“受害者情結”
記者:薛先生您好!剛讀完您的新著《怎樣做大國》。乍一看書名,可能有人會猜測,這本書會否與近年大行其道的“民族主義情緒”有關,但讀后發現,書中飽含憂患之思,而時下正值新中國成立60周年,“盛世”、“大國”呼聲正熾,如何看待自己此時的這種聲音?
薛涌:謝謝你讀了這本書。這是本頂風的書,不是本順風的書。是本憂患之作,不是歌舞升平之作。我希望讀者從這股“大國”圖書熱中辨認出我獨特的聲音。在舉國的“盛世”、“大國”呼聲正熾之時,我發出的聲音實際上是:“警惕中國泡沫!”
記者:中國領導人向國際社會莊嚴宣告:“我們是負責任的大國”,您如何看待“負責任”的含義?您感覺中國作為大國后,須對誰負責、如何負責?大家又如何做好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之民”?
薛涌:“負責”自然是意味著就自己的行為對他人所產生的影響負責,擺脫“受害者情結”。如果一有風吹草動,就覺得是別人欺負自己,就開始泄憤,那就是小國心態,而非大國氣概。舉個很簡單的例子。不久前,國內有一股強勁的“航母熱”,甚至掀起了民間捐款造航母的運動。在中新網論壇“中國造航母,你是否會捐款”的調查中,近萬名網友投票和參與討論,超過八成網友表示愿意捐款,其中有超過四分之三的網友表示愿意無條件捐款,很多網友愿意捐出一年的工資。
記者:您似乎對此感到意外?
薛涌:是的,我很吃驚。首先,現代國家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擁有強大的財政機器,能夠有效地支付國家的種種職能、特別是國防職能。靠民間捐款維持軍力,往往是國家貧弱或破產的癥侯,與中國當今的國力相差十萬八千里。
記者:但這至少反映了民眾的一種愛國心,而且“航母熱”似乎也與紛繁復雜的南海權益博弈有關。
薛涌:對。中國是世界上領土第三大的國家,有漫長的邊疆,加上現代國家建設的過程開始得晚,和鄰國之間在邊界上的歷史遺留問題自然比較多,有些爭議也不足為怪,但這和國家安全受到巨大威脅完全是兩回事。作為大國,處理這些事務本應該有足夠的信心,大可不必抱著半殖民地的心態,動不動就覺得別人要來瓜分自己。在南海和中國有海域爭議或潛在爭議的諸國,最大印度尼西亞,GDP不過五千多億美元,相當于中國的八分之一;馬來西亞不過是兩千多億美元的GDP,不足中國的二十分之一,還遠遠頂不上一個廣東省;再等而下之,菲律賓一千六百多億,越南不足九百億。這些大大小小的國家的GDP全加起來也不過中國的四分之一。和這些國家有一點小爭端,如果換上老撾、柬埔寨,也許會演成舉國動員的危機。中國這么一個世界大國犯得上嗎?這種心態,是屬于大國還是小國呢?更不用說,近年來,美歐等西方發達國家在軍事戰略討論中都特別強調航母這種大型戰爭機器的過時性、無法適應21世紀的戰爭。大家傾注資源發展靈活快捷的高技術小型武器,如無人駕駛飛機等。可見即使真有國家安全問題,航母也未必是個良好的解決辦法。
2坦率聊人心
心靈鎖閉比無知要糟糕得多
記者:其實,無論從物質力量還是民眾的心理上來說,大國的安全問題畢竟無法回避。
薛涌:對,航母確實規模巨大,有威風,更像個大國宣言,這或許是“航母熱”的重要根源。中國是否要建航母,還是留給有關決策部分審慎考慮。但“航母熱”幫助我們揭示出了民間的挫折感,以及這種挫折感為什么可能導致進一步的挫折。大國當然有國家安全的問題。但我們不妨問一問:作為一個普通中國老百姓,不管你生活在北京、上海等沿海發達城市,還是甘肅、貴州等落后的內陸地區,你最大的不安全感從哪里來?究竟是外國軍隊入侵、自己馬上成為亡國奴?還是生了病去不起醫院、干活拿不到工錢、下礦井一去不歸、退休后喪失了生活來源,或者房子被人強制拆遷?我認為后者才是對普通中國人的生活影響最大、中國所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只有解決了這些問題,中國才能充滿信心、高高興興地做大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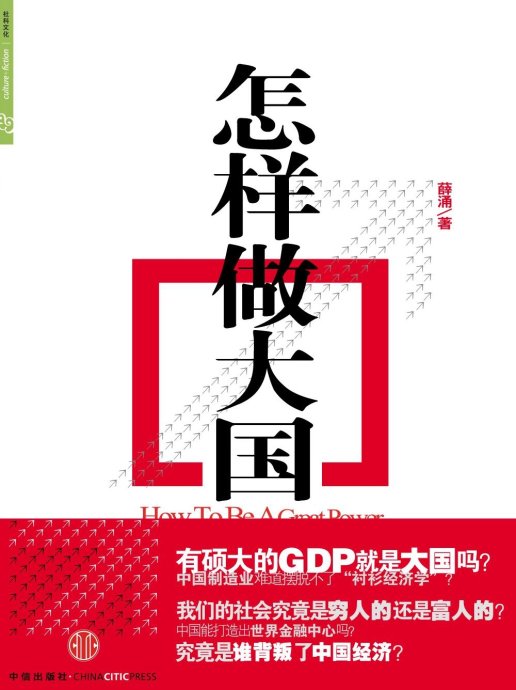
記者:您在書中有個比較,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社會封閉而人們心靈開放,而時下恰恰相反,是社會開放而心靈鎖閉,為何您會得出如此結論?
薛涌:我愛講一個故事。古代一位書生跑到山里的廟中向和尚討教。入座后,和尚斟茶,茶水滿出茶杯,和尚仍然倒個不停。書生大叫:“水滿了,快住手!”和尚說:“你的心就像這個茶杯。早滿了,還能聽得進什么新東西?”八十年代初的中國精神如同個空茶杯,大家覺得自己無知、不行,甚至有道德自卑感,現在則更接近于滿茶杯。這是我擔心的。舉個例子,現在許多人覺得自己對西方非常了解。有個流行的說法是:“中國對美國要比美國對中國了解得充分得多。”真是這樣嗎?美國人能把中國的一個村子幾十年的變遷原原本本地寫出來,中國人自己則還很少有這么詳實的研究。中國有一本研究美國一個小鎮的書嗎?明明不懂,卻自以為懂了,其結果不僅僅是無知,而且是心靈鎖閉。心靈鎖閉比無知要糟糕得多。無知并不可怕。特別是知道了自己的無知,就像八十年代的許多大學生一樣,學習起來非常快。心靈鎖閉則是自以為是,永遠也學不到新東西。
?
3坦蕩談期待
我認為中國要做到“人重物輕”
記者:您曾提出“中國不能永遠為世界打工”,把中國比喻為“一身肌肉的扛大包的工人”,時至今日,您感覺情況有多大變化?簡言之,中國能否或應當如何改變“打工狀態”?結果會怎樣?
薛涌:這個“一身肌肉的扛大包的工人”從18歲長到38歲了。干的還是同樣的活,而且沒有學習什么新技術。他48歲還扛得動嗎?改變這一狀態首先要接受教育和培訓,掌握新的技能,以求日后能夠做更高端的工作。可惜,中國缺乏這樣的教育投資。
記者:您認為中國要真正成為大國,首先是“人重”,要“人重物輕”,請問何解?而提倡“人重”的同時,我們又必須面對老齡化社會的洶洶襲來,如何不讓老齡化拖垮中國的經濟?
薛涌:“人重物輕”,簡單地說就是物廉人貴,東西很便宜,但工錢很高。我一直說中國要走高工資的道路。當然,高工資不是用計劃經濟的方法通過行政命令給老百姓漲工資,而是政府通過一系列的社會政策,對人口本身進行投資,以提高人口質量。比如,一個家長希望自己的孩子未來有高收入,應該怎么辦呢?那還不是從小給他上好學校,甚至傾家蕩產地供他上大學。為什么大家這么狂熱地為孩子的教育自我犧牲?這是因為生活的常識告訴人們這樣會有最好的回報。想想看,如果你在貧苦的鄉村當農民,孩子很聰明,你餓著肚子供他上了大學,后來他干脆還到常青藤讀了博士,他自己的生活不僅大為改觀,而且有足夠的能力養活年邁的父母。如果你不讓他讀書,讓他幫自己干農活,圖眼前的幾塊錢,還說這是趁他年輕力壯,發揮他的“比較優勢”,結果會怎么樣呢?恐怕是等你老了,他二三十歲,全家還在受苦。想想看,對下一代,你應該走前者的路還是后者的路?可惜的是,中國人在個人的生活中,都要走前者的路。但作為一個國家,卻在走后者的路。主流經濟學家們還拿出種種理由證明這后一條路的正當性。
我看到一則報道,20年前希望工程調查發現,農村貧困地區有100萬孩子失學,2003年全國婦聯調查發現,有100萬進城農民工子女在進城后失學。中國經濟起飛這么長時間,農民子弟還是繼續失學,只是失學的地點有所變化而已。那些幸運的民工子弟即使和城里孩子坐在一間教室里,學業上也至少落后兩年。新建起的“新公民學校”,本是為解決民工子弟的就學問題的。但是,學校招90個學生,政府“埋單”的只有30位,三分之二的經費要靠捐助。也就是說,一旦沒有捐助,那三分之二的孩子隨時可能失學。政府為什么不能解決這樣的問題呢?保證公民的義務教育,是政府的基本職能。怎么能把這種責任推給社會?政府為什么不能下一道命令:凡是能出示在本地區居住證明的居民(不管是買房還是租房),其子女有就近入學的權利,任何學校不得拒絕接收。政府根據學校接收學生的人數,對學校進行財政撥款。這樣,不是每個孩子的教育權利就都得到保障了嗎?這是發達國家常規的做法。我們過去可以說國家窮,沒有錢。現在已經是個大國了,這種理由說得出口嗎?
記者:這使我想到您在書中提到的,自己想在“小政府、大社會”后再加一個“強國家”,為什么?您感覺中國目前是一個“強國家”嗎?強與弱分別表現在哪些方面?
?薛涌:中國目前當然不是一個強國家。有那么多孩子失學,怎么能是強國家?公民基本的權利和福利得不到保障,怎么還能是強國家?大不一定是強。這就像體重大的人不一定健康,也不一定有力量一樣。
?
4坦然對爭議
我沒有“食洋不化”
記者:有沒有人批評過您“食洋不化”?畢竟從時空上看,您離中國的現實不能說沒有距離。您平時對大陸時事進行判斷的信息渠道都有哪些?
?薛涌:所謂“食洋不化”,是目前國內對我典型的批評。在我看來這也是中國心靈鎖閉的證據。什么叫“食洋不化”?你首先要“食”,然后才有化不化的問題。中國對西方的什么東西吃透了呢?老實說,就像電視、汽車這些最基本的東西,我們也要靠人家的部件,否則不出地道的產品來。可以說,我們對“洋”,對西方的東西,首先還是學不會的問題。等你學會了,才有對人家說人家的東西是否合你的用。打個簡單的比方,你做不出豐田那么好的車來,卻罵開豐田是“食洋不化”。人家豐田當年是怎么樣呢?人家先“食洋”再說,把美國乃至世界的汽車技術吃透,最后舍棄一些不符合自己理念的東西,創出自己的品牌。我還堅持自己一貫的主張:中國目前最緊迫的任務是學習西方,一定要學得地道。中國文化,也只有西化后才能復興。
你可以說我離開中國的現實有距離。比如,這十幾年北京“故居”門口蓋了多少樓,我一點不知道。老母說我回來會找不到家門。這我當然承認。但是,我畢竟在中國生長了三十三年。一個國家的精神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很難變。我和國內的朋友保持聯系,參與國內的公共討論,看國內的報紙,也看國外對中國的報道,有時角度還更多些。我吃驚的有時并非那些令人難以置信的變化,而是那些難以置信的倒退。比如現在的大學生,沒有我們當年那么富于批判精神,歌功頌德的熱情非常高,對官位非常崇拜。我們那代人舍棄的許多東西,被下一代又揀了回來。所以,中國雖然有許多變化,但中國我還是認識的。我相信我的言論對中國很有幫助。我的寫作,確實也受到許多國內讀者的歡迎。在我看來,誰也沒有資格指責別人“食洋不化”,還是讓讀者自己判斷為好。只要他們覺得我談的東西有意思、愿意掏腰包買我的書,就說明了我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