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dǎo)語:在當(dāng)下的中國,很多女人往往對年齡有一種焦慮感,似乎如果不在指定年齡發(fā)生一些事情,就會被時(shí)代所拋棄,成為孤家寡人,社會邊緣群體……
35歲是女人的一道坎兒嗎?
25 歲以后,很多女性就開始以結(jié)婚為目的和人交往,在她們的時(shí)間表上,30歲成為結(jié)婚的最后死期限。這在很多女性看來就是花期結(jié)束的時(shí)候——過了30歲,似乎 女人就是早市上的黃瓜到了晚上,是要拋售的時(shí)候了而35歲,則在很多女人眼中是另一個死期限——必須在35歲前有一個孩子。一般來說,如果35歲前孩子已 經(jīng)到了上幼兒園的年齡,這在很多女人看來,就是一種功德圓滿的象征。
但往往到了這個時(shí)候,也是很多女人人生第一波危機(jī)的時(shí)刻。
這個危機(jī)叫做“自我標(biāo)準(zhǔn)”的危機(jī)。在此之前,可能很多女性都會以父母的意志為軸心,從工作到情感到生活,都是按照父母的要求和標(biāo)準(zhǔn)來制定的。當(dāng)工作進(jìn)入軌道,生活也開始穩(wěn)定,孩子也沒有那么占據(jù)自己的時(shí)候,卻發(fā)現(xiàn)老公早已遠(yuǎn)離了自己的視線。
這時(shí)候,往往就是到我們要還債的時(shí)候了。豆腐渣工程往往都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最大的危機(jī)在于,我們用自己的腳穿別人的鞋——我們該從事什么工作,嫁什么樣的老公,什么時(shí)候有孩子,該怎么過日子,如果這些都由父母來決定的話,這就意味著我們根本沒有青春期。
沒有青春期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你本來應(yīng)該在12歲開始思考人生,現(xiàn)在到了20年以后才開始。
12歲思考人生的好處是什么?你那時(shí)叛逆一下,最多也就是離家出走,考試掛科什么的,最多休個學(xué)也不算什么。
現(xiàn)在你都拖家?guī)Э谧恿耍藕鋈话l(fā)現(xiàn),這工作其實(shí)你一點(diǎn)兒也不喜歡,這個伴侶根本不是你認(rèn)真為自己選的,甚至連孩子的到來你也沒有準(zhǔn)備好。
其實(shí),就是一句話:我還沒玩呢,怎么就開始了后半生呢?這就好像是建設(shè)一個大樓,如果在打地基的時(shí)候,我們就開始有調(diào)整,就算推翻從來,成本也小得很,現(xiàn)在樓都建起來了,成比薩斜塔了。
父母告訴我們:只要按他們說的做,我們就會幸福,只要我們工作穩(wěn)定,有一個不離婚努力賺錢的老公和一個活潑可愛的孩子,我們就會有幸福。
可是到了這個年齡,我們還能這樣騙自己嗎?
告訴自己其實(shí)不想要夫妻之間的溫存,沒有情感的慰藉和身體的激情的需要;
告訴自己其實(shí)找一個人讓自己心動的男人一點(diǎn)兒都不重要;
告訴自己,其實(shí)對一個男人的呵護(hù)和渴望以及欣賞的需要只是一種幻想;
告訴自己每個晚上,一個人睡在床上孤枕難眠只是做一個賢惠老婆的必要條件而已;
告訴自己,老公很上進(jìn),天天加班,這很好,雖然這個家已經(jīng)成了旅館……
這個時(shí)候,很多女人都已經(jīng)放棄了作為妻子的需要而只是要求男人履行父親的職責(zé)而居然不可得。
可是,誰為你這幾十年的沒有女人味道的生活負(fù)責(z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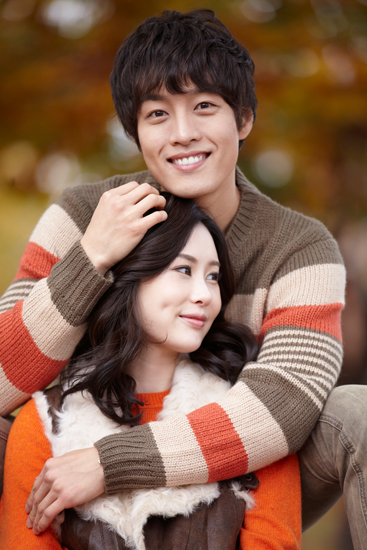
35歲是一個女性開始全面覺醒的時(shí)刻
最大的危機(jī)在于,你發(fā)現(xiàn)父母的話不靠譜了,他們的標(biāo)準(zhǔn)某種程度甚至對你是一種毒害。你需要形成自己的標(biāo)準(zhǔn),完成對自己的解放。
35歲,往往是一個女性開始在性、心理、心靈、自我和親密關(guān)系全面覺醒的時(shí)刻,她在這個時(shí)候,往往才開始真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才知道自己是誰。
但這個時(shí)候,女人們往往就會發(fā)現(xiàn),自己因?yàn)檫@些年在婚姻中積淀的塵土,已經(jīng)不想為那個“熟悉的陌生人”付出了。
或者她甚至發(fā)現(xiàn)自己之所以沒有那么多投入的愿望是因?yàn)樗麄儚囊婚_始就是一種湊和,而非真的動心而在一起,也就是說兩個人本來情感基礎(chǔ)就很淡漠,到了危機(jī)發(fā)生的時(shí)候,他們自然很難有真正的投入了。
其實(shí)這個時(shí)期,也是女人一生中最成熟的時(shí)刻,無論是自身的女性魅力還是思想的成熟,還是經(jīng)濟(jì)的獨(dú)立,都是一生中的最高峰,此時(shí)掙脫父母意志的羈絆,尋求一種為自己負(fù)責(zé)的人生是最合適的機(jī)會。
其實(shí)青春期的主題就是分離——個體化:分離是指,我和父母分離,我和老公分離,我和孩子分離,這種分離不是說要和誰決裂,而是說我的感受,我的思想和我的行動都是自發(fā)和自主的。
而一個孩子和父母是不能分離的,孩子痛苦,父母就感同身受,相反,父母痛苦,孩子就內(nèi)疚不已。這種共生的狀態(tài),讓我們無法區(qū)分什么是我的幸福,什么是父母的幸福。
這種分離遲早要完成,因?yàn)槲覀兪怯兄约旱囊庵竞透惺艿模@種以犧牲為要旨的文化不得不讓位為雙贏的文化。
我們需要首先找到自己的需要,也找到父母的需要,以一種談判的心態(tài)努力找到雙方的重合點(diǎn),不光是要自己為對方而調(diào)整,也尋求對方為自己而調(diào)整。
我們需要學(xué)會部分為對方負(fù)責(zé)而無法對別人“無限負(fù)責(zé)”。學(xué)會為自己買單,而不為別人買單。我們需要知道自己的有限性,那就是我們無法讓別人永遠(yuǎn)幸福,永遠(yuǎn)快樂,那不是我們的能力所限。
我們需要學(xué)會不斷自我肯定,以及到能夠肯定我們的人群尋求肯定,而非一生都糾纏著沒有能力肯定我們的父母尋求他們的肯定。
每一個選擇都有其代價(jià),而有些喪失,就是喪失,它不會是大片里的大結(jié)局,生命不是手指甲,而是我們的手指,斷了就不會再來;比如父母的情感可能不是我們作為孩子可以維系的;比如發(fā)現(xiàn)浪漫其實(shí)只是因?yàn)槲覀儫o法面對喪失而有的一種幻想……
此刻,我們才成為我們,而融入了比父母更大的存在。
那時(shí),我們才能做出決定,而這些決定往往是需要絕大勇氣和絕大能量,甚至是傷筋動骨的。
但這是必然的,因?yàn)檫@是一個纏綿了幾十年的病痛,它定義了我們,而我們現(xiàn)在要做的,是重新定義我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