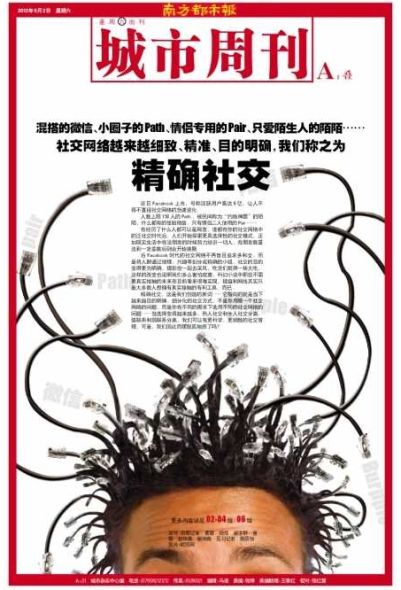
南方都市報城市周刊封面:精確社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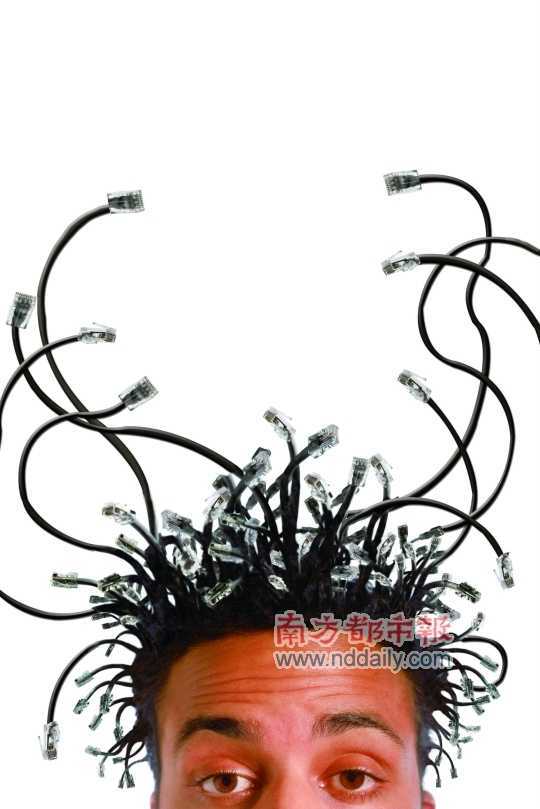
混搭的微信、小圈子的Path、情侶專用的Pair、只愛陌生人的陌陌……
社交網絡越來越細致、精準、目的明確,我們稱之為
近日Facebook上市,號稱活躍用戶高達9億,讓人不得不直視社交網絡的急速進化。
人數上限150人的Path、被民間稱為“約炮神器”的陌陌、什么都有的怪胎微信、只有情侶二人使用的Pair……
在經歷了什么人都可以是網友,誰都在你的社交網絡中的泛社交時代后,人們開始探索更具選擇性的社交模式,正如現實生活中在沒朋友的時候努力結識一切人,在朋友數量達到一定基數后則會開始挑剔。
后Facebook時代的社交網絡不再盲目追求多和全,而是將人群通過地理、興趣等劃分成精確的小組,社交的目的變得更為明確,攝影控一起去采風,吃貨們就得一塊大吃,這樣的改變也說明我們多么害怕寂寞,科幻小說中那些不需要真實接觸的未來在目前看來很難實現,鍵盤和網線其實只是大多數人想擁有真實接觸的有利工具,而已。
精確社交,這是我們創造的新詞———它指向的就是當下越來越目的明確、細分化的社交方式,不是你用哪一個社交網絡的問題,而是你在不同的需求下選用不同的社交網絡的問題———當選擇變得越來越多,熟人社交和生人社交分離、強聯系和弱聯系分離,我們可以有更科學、更細致的社交管理,可是,我們因此而擺脫孤獨感了嗎?
嘖嘖,連嬰兒都有一批專屬的社交網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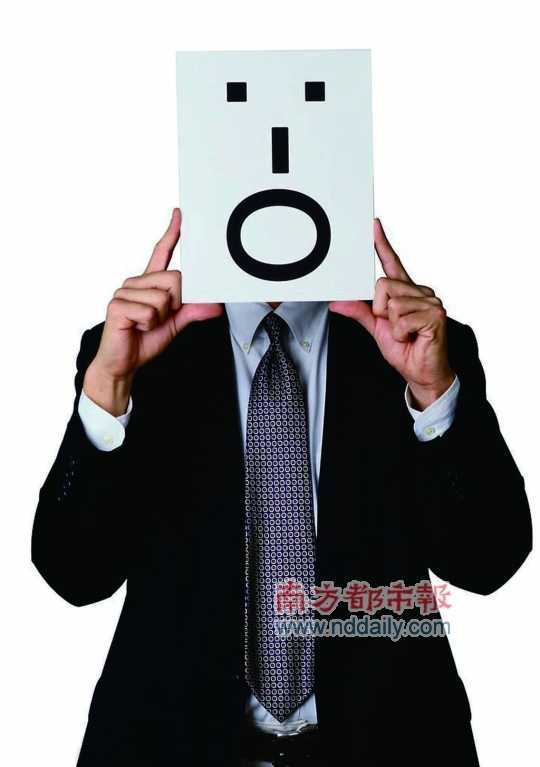
這個社會的胖子會越來越多!據美國加州大學圣迭哥醫學院和社會科學部教授James Fowler研究,社交網絡有傳播肥胖的可能。雖然其發生過程尚不清楚,但肥胖與社交網絡一旦建立關聯,減肥的時候,還需要戒社交網絡嗎?
不過,想戒更難!一周前的Facebook上市,就已經被認定為互聯網的第三次浪潮。在這社交網絡的浪潮之下,躲得躲不了被滅頂是一說,想要不濕身?除非你不用電腦,或者穿越回歸到黑白版本的諾基亞、摩托羅拉年代。況且,社交網絡許諾的是一個燦爛的未來。一個有著英雄惺惺相惜的圈子,一個有著近距離時空關系的現實,一個能夠舌燦蓮花、喋喋不休、無人嫌你煩的場所。依照麥肯錫只坐頭等艙的邏輯而言,說不定,一個社交圈就等你免費坐一趟頭等艙,可以售出自己的產品、興趣、智慧,甚至本人。當然,前提是你得找到社交圈。因為,在各種社交網絡橫行的當下,你得分得清,你在售賣頂級魚翅的時候是不是面對的是一個環保主義者。
大學生、鄰里、吃貨、書蟲都有自己的專屬網絡
5月29日,Facebook的股票狂瀉近10%,跌至30美元以下,而幾天前,這個互聯網童話的男主角扎克伯格才剛剛把自己在Facebook上個人頁面狀態改成了“已婚”。有人說,這是一個蜜月的開始,另一個蜜月的結束。
其實,如此說法未免目光短淺、心胸促狹。殊不知,即便Facebook的股價猶如暴雨天起航的飛機顛簸不已,但起飛就已經像是刺向華爾街天空的一針雞血———更多的人懷揣信奉上帝般的虔誠認為,前方風急雨驟,但分分鐘就會萬里晴空。因為,Facebook們掀起的是互聯網的第三次浪潮(前兩次是w indow s操作系統的建立以及雅虎、G oogle的上市)。在社交網絡這個系統中,Facebook就像太陽系中的太陽處于中心位置,但一些新型的社交系統,例如,P ath、陌陌、Pinterest、Instagram、T hum b、Foodspotting亦在以自己獨特的所在吸引用戶。新星不斷誕生,黑洞不斷發展。當然,其信仰的背后是基于這些社交網絡的革命性。
有關網絡社交,早在江湖上流傳這樣一個質疑———你永遠不知道電腦的那頭是人是狗。而新興的社交網絡則是徹底將這種想象力的苗頭按壓至瞎掰的谷底。不管是定位社交、興趣社交、圈層社交,各種細分的、精確的網絡社交的目的都只有一個———關系,人與人的關系。除非對面的那條狗亦有大學身份、懂得品鑒1982年的波爾多紅酒,或者也讀得懂康德。
關系,說起來挺庸俗。但話糙理不糙。唐寅的雅集不就是拼酒、泡妞興趣班嗎?常春藤盟校不就是政客們的歡場嗎?網絡社交不過就是將這古今中外的社交網、興趣班搞成了“相見不如懷念”的意淫版本,當然,有些人更以見面為直接目的。且別說大學生、鄰居、閱讀、美食等各種細分社交網絡的風行,就連嬰兒都有了自己的社交網絡,諸如Totspot、O dadeo、Lil‘G ram s、K idm ondo等一批嬰兒社交網絡全都是在貫徹關系“從娃娃抓起”。
不管二逼或天才,你的朋友圈不會超過150人
在現實中看不見的關系網,在這社交軟件中卻愈發顯得明顯。看著洋洋灑灑的關注名單,自豪得要像交際花接受眼光膜拜時頻頻且優雅地點頭。不過,亦有孤寂凄涼的時刻———當你振臂一呼,指望朋友能給予襄助之時,甚至只是想邀得陪你過周末的人,那些名字沉默得就像黑洞一樣,意興闌珊到恨不得把這幫人與軟件一并刪除。這叫連鍋端。而在這混沌錯亂的年代,在這個人情寡淡的社會,大把的鍋正煮沸著,大把的鍋也正讓你恨不得連鍋端。
Path、朋友圈的模式正是一劑心靈雞湯。看著微博那幾千、幾萬不是僵尸的僵尸粉,平日里再活躍的強關系也難以以朋友的姿態出現。而在Path與朋友圈中,這種弱關系則會被打破,爛友濫情的社交關系被避免。
英國牛津大學進化人類學教授羅賓·鄧巴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人們可以擁有1500名社交網站‘好友’。但只維持與現實生活中類似的大約150人的‘內部圈子’。社會圈子的數量增加,人腦的智力負擔顯然要呈現級數變化。”而這150定律從原始社會開始即是如此。一個部落超過150人就會慢慢分化成兩個,羅馬軍隊的基本單位是150人。寄希望于網絡可以拓展社交圈,甚至期冀社交圈無限大的人怕是只能目光迷離地看著這“寥寥”150人興嘆。
城市沙龍式的社交注定要回歸到家庭式聚會。分享視頻、分享照片、增加表情顯然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這種分享勾勒出的是更親近的私密關系。如果說,Path通過150個朋友人數上限刻意勾勒出客廳式的私密的話,那么,Pair就完全是情侶之間的閨房親密了。在這封閉的二人世界,竊竊私語、卿卿我我、恩恩愛愛。早知有此社交軟件,某個把微博當Q Q使用的公務員在與美女調情之時,就不會引來無聊看客的集體圍觀了。
簽到、約炮、鄰里服務……LBS消解距離,卻又淪為幫兇
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基于位置的服務),但在坊間,它被稱為Lo-cation Based Sex,中文為,一切不以泡妞為目的的社交網絡都是耍流氓。
這是豆瓣上一個自稱“馳騁社交網絡多年,向來以智慧而非蠻力約炮”的青年自述:“在數位素未謀面或僅有一面之緣的女性輪番摧殘下,我的意志和三觀幾近被擊垮,終于在兩周前默默地刪除了陌陌。”這位青年筆下的陌陌就是大名鼎鼎的“約炮神器”。當然,亦有人天真地奢望在陌陌上能找到真愛。
除了陌陌之外,鄰居社交、附近的人以及各種簽到都是對真實的物理距離的回歸。在烽火、家書、電報、電話的時代,跨越距離、消解距離是人類的愿望。而進入網絡社會之后的天涯咫尺零距離是幸福,亦是劫數。不需要眼巴巴地絕望地看著遠方的人時,反而愈發陷入對周邊人的好奇之中。網絡誕生的意義在于消解物理的空間距離,卻反倒過來,又服務于物理的近距離,成為物理空間的幫兇。泡夜店時,即便是孤零零地坐在一旁,不敢與一旁的美女搭訕,也想知道究竟身邊的這些人是何許人物。長夜漫漫,孤枕難眠,青燈草床輾轉千次,還不如找尋同樣失眠的人慰藉。找尋物理空間中的“知音”,LBS不僅是給了狗一樣的鼻子,還順帶附著了丈量距離的雷達。
不過,正如成敗蕭何。陌陌等定位服務自然是提供了與帥哥、美女們鏖戰的機會,同時倒也容易泄露馬腳被哪個正室追殺,或者是陷入仙人跳的圈套。而鄰居除了能相互守望的同時,亦要擔心是否會被某些不良用心的鄰居利用玩一場尾隨或者整蠱的游戲。因為,有美國機構調查研究,15%的受訪者會在社交平臺上表示自己已離開家,35%的用戶會利用智能手機公開目前的所在位置,而盜竊前科犯中亦有78%的小偷會利用定位軟件盯梢“客戶”。
以興趣為主題的社交網絡不過是古代興趣小組的升級版
在這世上,有人會為伯牙斷琴,有人會聞雅香而動。每個人都在找尋自己的磁場。并且,在這磁場之中結交守望相助的知音。他們在現實中的關系很淺甚至是沒有,但大抵都有重英雄惜英雄,相見恨晚的情愫交織。
而在T w iitter、Facebook、微博這些社交網絡中,英雄們往往有生不逢時的錯覺。他們激昂地抒寫詩歌,卻被水泥森林般的死寂掩埋激情;他們給出自己小兒的一張“尿床”寫真,卻也被捧臭腳者誤以為有驚天巨作問世;他們拿出一塊家傳的上好寶玉,只差上面沒寫上“莫失莫忘仙壽恒昌”,卻被一幫圍觀者質疑是真是假。只嘆:我很憂傷,我很厭煩,我很憤怒。我空有粉絲成千上萬,卻仍缺知己者一人。我恨不能兼容于世人,通達于天下。
一個音樂狂再也不用在Facebook接收那些與你品味不一的朋友們的音樂分享了。聽起來,有些背信棄義,但實在是件快事。基于社交圖譜的朋友圈往往是同學、同事,時過事移,恰同學不再少年,稀少了的不僅是頭發,還有共同話語。同事亦是共同糾結在職場中,遠近親疏難控,怕是一時難以將興趣完全分享。而興趣網絡則是呈現出高度近似的氣息圈地,興趣讓這些英雄們心氣相通,當然,二逼與屌絲們也一樣找到自己的歡場。只要有共同興奮點,即便相隔天涯,亦會嗅著個鼻子湊到一起。
不過,在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人文學院教授于長江看來,這種興趣社交網絡不過是興趣小組在網絡時代的延續而已。“古今中外自有各種各樣的興趣小組,而網絡不過是充當了更便捷工具,從社會組織與交往方面沒有實質性的變化。”他認為,這興趣社交不過是鳥槍換炮而已。
Path:小圈子內的熟人社交
Path是什么?只有熟人能看到,并且有人數上限
Path翻譯成中文就是小徑的意思,雖然是外國人研發的A PP,卻很有禪意,曲徑通幽處不正是高級私人V IP會所那旮旯嗎?Path強調的就是這一份私密性。
Path的牛逼在于,它是排斥陌生人的:不通過好友申請就無法看到你發的內容,并且有一定的好友上限,不能無限分享給所有人。
其實,想要證明一個A PP是否真的好用受歡迎,還有一個特別簡單的方法鑒定———騰訊山寨它了嗎?在騰訊微信最新更新的4.0.1版本中,新增了一個功能叫“朋友圈”,活脫脫就是國產Path,從側面充分證明了Path的價值。
“如果說Facebook是城鎮的話,那Path就像是一個家庭,它們分屬于不同的社交網絡,但都不可或缺。”我們需要和陌生人打交道,但我們更愿意向親朋好友敞開心扉,尤其是重視小圈子的中國人,Path的出現簡直如同福音。
Path玩什么?你的廢話和秘密只有熟人才能看到
當你對某事件發表看法時卻擔心與老板政見不一,猶豫后還是按了退格鍵;又當某憤青愛用各種社會新聞刷你的屏,但出于同學關系不得不保持關注;某悶騷女每天必須上傳十張她的同一角度同一pose的自拍照如影隨形,但她是坐你隔壁的同事無法屏蔽……你的網絡社交圈逐漸越來越像business而不是原本單純的友誼。總有些話你只想說給某些人聽,總有些事你不想某些人知道。
第一代Path添加好友上限人數為50人,更新后增加到150人,也就是說,必須是熟人好友,才會進入到你Path好友的名單,你發起Path來也更像跟朋友嘮嗑而不是公共演講。雖然有50人的上限,但其實最佳的Path友數量應該是10名左右,這樣你既可以放心地刷屏不用擔心被鄙視,也不用看太多的刷屏而接受過多垃圾信息。
Path還有一個貼心功能就是狀態只分為醒著和睡著,躺在床上完成了一天的表達欲望之后,點擊月亮鍵,屏幕就會暗下來,而你的好友就會收到“某某在某地睡下了”這樣一條狀態。更新中文版之后,如果你剛好睡不著又醒來打開Path,就會自動發出一條“某某在某地夜不能寐”的狀態,這時如果有好友也正好醒著,天就可以聊起來了。
Path怎么玩?
1.欲擒故縱型———用來鄙視其他大眾化社交模式。秘密嘛,就是沒有人知道就沒有了作為秘密的價值。所以,有的人就是想告訴別人我有東西不告訴你,就像當年的加密博客,不想說你大可以爛在肚子里,非要搞得一副諱莫如深的樣子才高端嗎,Path可以盡情滿足你這方面的需求。你可以截圖一張,再發上微博、人人、豆瓣這種開放式的社交網站,說幾句曖昧不清的話,比如“還是Path比較清凈”、“哈哈哈某某某的Path好好笑”等等與廣大人民拉開距離的話,充分體現了“我有你無”的優越感。
2.華山之巔型———明星在上面放心地自爆隱私。這種類型的Path屬于高度機密,不少明星名人申請了Path就這么玩,好友嚴格控制在10個以內,說的發的都是自己真實生活,真是實在憋不住了一定要跟人分享的東西:比如今天又買了個兩萬的包,拍了某某廣告還沒上搶先在Path上傳一點花絮,見不得光的女友合照發一發……這種玩法已經不僅僅是社交網絡的分享機制,更考驗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玩到這個份上,真的有點決戰紫禁之巔的岌岌可危感。
3.話癆刷屏型———更像朋友之間的交換日記。“我要快點介紹幾個朋友玩Path,不然每天都被你刷屏好痛苦啊!”被朋友拉來開了Path的小蔓對朋友訴苦道。原本在微博上惜博如命的人,到了Path上立刻盡顯話癆本色。不用擔心刷屏會被不熟的朋友翻白眼,也不用擔心會被上司覺得你是個話多不穩重的人,更不會被原本仰慕你的小粉絲發現你原來常常百無聊賴。Path副總裁馬特·范霍恩表示:“Path是一個較小的網絡,針對你生活中最親密的好友和家人設計,因此人們也愿意分享更多內容。”這就意味著,相對于微博、豆瓣網、Facebook等等這一類開放型的社交網站,Path更像朋友之間的交換日記。
Pair:情侶之間的社交,異地戀的福音
Pair是什么?人數上限2人,親密社交
當前最主流的社交網絡形式有兩種,一是基于關系圖譜的Facebook,二是基于興趣圖譜的T w itter,當然,在越來越多元化的社交方式需求下,無論是基于關系還是興趣圖譜的圈子都已無法滿足更精細和個性化的需求,人們普遍陷入了認識的人越來越多,親密的圈子越來越小的困惑中,于是,基于移動私密社交的Path和情侶專屬社交應用Pair應運而生。
從Facebook到Path,再到Pair,我們看到好友上限人數從5000人縮減到150人再到2人。在簡單的數字背后,是社交網絡對個人情感生活關注的側重點轉變,更是當下社交網絡所精細化和個性化現狀的體現,由此也決定了他們的產品屬性:大眾社交,私密社交,親密社交。
愛她,就為她寫一個APP吧
知道理科男是怎么拍婚紗照的嗎,答案就在《生活大爆炸》的第五季最后一集中,他們的攝影師是谷歌衛星,不花錢就能讓全世界都知道,理科男浪漫起來,地球都會顫抖。不過《生活大爆炸》畢竟是虛構的次元,再好的情調也不過是像素拼湊的。
而現實中的理科男在用代碼給女友制造驚喜的時候,也順便造福了人類。這個理科男叫王俊煜,那幾行代碼叫做“Together”。
“去年12月,我結婚了。我的對象是朱大力。”這是王俊煜在博文《T here‘s anappfor you》中跟公式一樣清晰直接的開場白,然后,她就去山景城出了三個月差,直到4月1日才能回來。
“三個月兩地相處的時間里,用G oogleV oice打電話,用G oogle Chats進行文字和視頻聊天。還有,Line、Path、K ik等各種應用都是我們保持聯絡的方式。”分隔兩地對誰都是一個挑戰,不管通訊有多發達,“始終還是覺得有很多缺憾。比如,思念對方的時候,還是沒有辦法知道對方在做什么、想什么。”
徐志摩在思念對方的時候會寫一首詩,而王俊煜則是寫一個A PP,“大概在2月份的時候,開始構思一個給情侶保持關系用的應用。”2月底的時候他開始學習安卓開發,然后利用周末的時間來開發,“和所有的創業項目一樣,這個項目的開發過程也很曲折和懷疑人生。花了六七個周末的時間,終于完成了第一個版本。”
其實,Together的基本想法非常簡單,就是兩個人一起拍照片,一個屬于兩個人的照片墻。打開它,拍照,馬上就會上傳,女生拍的照片用紅色表示,男生拍的照片用藍色表示。不需要點好多次按鈕,也不需要在通訊錄的幾千個人里面去選擇要分享給誰,不需要進行各種后期處理,沒有多余的功能,沒有贊,沒有評論,也沒有分享,也沒有濾鏡。拍了照片,對方就能看到,在Together的世界里,絕對可以海枯石爛天荒地老,前提是要有網絡信號。
這個應用已經在G oogle Play發布,遺憾的是目前僅支持G alaxy N exus并需要邀請。
天生一Pair(對),情侶可以玩“拇指吻”
T ogether不同于F acebook、T w itter、Instagram甚至Path,在社交上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它走了一條少有人走的路。其實,這種針對
情侶的應用不止Together一個,相對成熟的還有Pair。
和Together一樣,Pair也是誕生于成員自身的需求,Pair是5個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滑鐵盧大學的同學創建的,他們離家來到美國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亞,其中3個小伙子非常想念女朋友,于是通過一個24小時的馬拉松編程做出了Pair的原型。Pair的口號是:Betogether,w henyou‘re apart.Pair只允許情侶間一對一使用。
Pair讓喜歡成雙成對的情侶們,有機會把愛的二人世界從現實生活延伸至網絡虛擬空間。比如Pair允許情侶之間不受限制地發送甜言蜜語(可以像微信一樣,發送語音、文字、圖片、位置)。
Pair除了擁有Facebook、Instagram或者Path上都有的照片和信息分享的基本功能外,它還包含了情侶專屬的功能。例如,其中包含叫做“拇指吻”的甜蜜想法。情侶在屏幕上按下拇指,用戶拇指接觸屏幕的任何區域時,它都會顯示指紋,當兩個拇指對齊時,兩人的手機就會震動起來。
更加貼心的是,每個Pair賬號只能與一個賬號配對,所有的數據都存儲在云端,當你與對方解除配對關系后,你將無法訪問這些數據。當你和對方恢復關系,以前的數據會自動恢復。誠然,或許由于受眾群體有限,Pair始終無法變成像Facebook那樣大眾化的社交產品,但Pair的可貴之處正在于為專屬人群保留了曾經最甜蜜的回憶,無論是攜手共度或各奔東西,曾經的親密往昔都幻化成字節數儲存在遠方持續運轉的服務器里,變成永久的記憶。
微信
精確社交時代的四不像怪胎
微信是什么?
回顧一下,你的手機應用里什么時候從各種“某聊”或者“某信”,只剩下了一個“微信”?大多數人會回答:哎?還真是這樣,除了微信,其他的用著用著就不用了。不過要是一部攝像機把這個過程拍出來,那可真是一部手機通訊和社交界的《甄嬛傳》。
作為“皇上”的你大概還以為后宮太平無事,“妃嬪”和諧幸福,還以為想用哪個軟件都隨著你,其實你們的寵妃們早就在競爭中長出了三頭六臂,八面玲瓏,或者競爭不過香消玉殞。
就拿我們三頭六臂“女主角”來說,2011年,微信一共發布了45個不同終端的版本,平均1.15周發布一個。她的slogan從“能發照片的免費短信”、“最時尚的手機語音對講軟件”,變成了“最火爆的手機通信軟件”,最終到了今天的“微信,是一種生活方式”,所以,她笑得最好,至少目前為止,不知能否笑到最后。
在經歷了45個不同版本的變化,微信是“一種生活方式”這個牛逼又曖昧的說法卻無法告訴大家:現在的微信,到底是神馬?
回答一:它是可在手機上發語音短信的東西!
正確。2010年加拿大手機IM軟件(說白了就是手機上用的MSN和QQ )KIk“一夜爆紅”創造了15天增加100萬用戶的記錄,擅長“借鑒學習”的騰訊哪里坐得住,據說光是他們內部就有5個團隊競爭,最后還是廣州郵箱團隊搶得先機,1.0版本的微信出爐。
緊接著talkbox又給騰訊提供“靈感”,2.0版的微信配備了語音信息,這簡直是老花眼患者的巨大福音,從而也揭開了許多80s、90s抱怨父母喜歡語音騷擾的序幕。
回答二:它是約炮利器!
咳咳,實在沒法說這個答案不正確。
微信在2011年8月推出的2.5版本,加入了LBS功能,就是“查看附近的人”,這是約炮界發展的里程碑,雖然微信產品總監劉樂君聲稱這個功能是“走進生活”比如拼車或者賣二手產品,天知道這位總監到底是真純潔還是假正經,不過這次用戶“噌”地迎來爆發性增長。
直到3.0版本出現后,微信“約炮三駕馬車”全部現身:搖一搖、漂流瓶和查看附近的人。無論是搖一搖看看“誰和你同一時間搖”還是“撿起一個漂流瓶聽一段五音不全的歌”,微信徹底開啟了和陌生人打交道的“社交時代”。
回答三:它是“搞亂生活”的生活方式
這個回答無可挑剔,特別是在4.0版本全球上市后。
4月19日,微信4.0版本浴火重生,它看上去更加像一個社交平臺了:每個用戶多了一個在線的個人相冊,可以創建和存儲圖片;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可以用半公開的形式發布圖片和文字信息(包含粗略的位置信息),并分享到騰訊微博……
有人調侃:禽獸啊,先是蹂躪了kiktalkbox,現在連Instagram和Path也不放過。的確,單從結果上看,微信是這場“精確社交”的浪潮最成功的沖浪手,十八般武藝集于一身。4月25日,4 .0微信在港澳臺內地四地的appstore社交類別占據了榜首,雖然它不是第一個玩家,也沒發明什么“獨特的動作”。
可是這樣的“貪心”,可能意味著“失控”。
在它還是第一個回答“免費發語音短信”時,微信以通訊錄為主要鏈接,這是鐵當當的“強聯系”,沒有什么比你的電話號碼本更扎實的社交關系了。
但是到了第二個回答“約炮利器”時,陌生人的“弱聯系”也進入了。好吧,無論你和認識或不認識的人免費語音至少都是私密進行的,比如說,你那幾個女友應該不會知道彼此的存在(呃,忽略導向偏差,就事論事吧)。可是當進入第三個回答階段時,微信有了太多社交網絡的功能,但是用戶卻是熟人和陌生人夾雜,新朋友舊朋友混亂。你上傳的一張照片,熟人和陌生人都可能看到和評論,若是你的兩個女友同時評論了這個照片,那么你的生活恐怕要面臨一個“崩潰式結果”。說白了,用戶關系越亂,平臺越不穩固。
在現在社交網絡越來越精確、越來越注重功能區分的時候,微信像個怪胎,遠遠看上去是個身材火辣的美妃,但是走近一看不禁大驚:“愛妃!你怎么兩個腦袋,每個腦袋六只眼睛!”皇上,你可長點心吧。
可能會流行的社交網絡們
Burpple
1.愛得瑟的吃貨請聚在一起
Burpple:根據《移動新發現》的描述Burpple是一款綜合了Path和Pinterest元素的美食分享應用,讓人們隨時隨地分享美味佳肴照片,發現新的美食創意。
這款應用在亞洲市場上特別是中國人群中應該會迅速得到響應,澳洲人都知道亞洲人喜歡在餐前為食物留影,要不怎么會建立“亞洲人拍食物的照片”網站!而大部分喜歡轉發陸琪、作業本、星座,還有各種心靈雞湯的不擰巴姑娘們更致命的共同愛好也是非得告訴所有人,每天吃了什么。肯德基他們拍,標準句式是:“啊,今天要肥死了!”星巴克也得留念:“抹茶星冰樂,你怎么還不來啊?”大排檔,五星級酒店,私房菜館,只要是個吃飯地就有人熱衷于分享,但有個問題是盡管有些同樣無聊的人會回應,大部分人看見自己的社交網絡頁面被滿屏幕食物給占領了,心里依舊會罵娘吧。
所以Burpple的誕生給這群愛拍照分享的吃貨們一個集中地,圈一塊得瑟去吧。
不過讀圖為主的社交網絡有個更明顯的優勢:直接。這群吃貨們用美食圖片直接刺激饑腸轆轆的加班人,而他們同時用美食照片為商家做了最直接良好的宣傳,同Path一樣,Burpple做的是熟人社交,誰都知道來自朋友的餐廳推薦遠比廣告有效,所以已經有餐廳準備入駐該社交網絡,用圖片去直觀地推薦餐廳了。
2.和線上愛吃的人一起面對面共進晚餐
Grubwithus:花費25美金得到的與陌生網友真實相聚的機會,大家一起干的事是吃飯。
這是一個充滿悖論但卻意外被看好的社交網絡,盡管社交網絡的意義是希望用戶們突破地理界限無障礙交流,可不得不承認的是人們依舊更信賴現實中的朋友,真實的碰面才是他們心中最深的渴望。
于是用晚餐這樣一個概念,把網友從線上拉到線下的grubw ithus發展勢頭兇猛。它對地域的限制相當嚴格:現在的服務區域只在美國少數幾個大城市,且能接受聚會的餐廳還在發展中,但人們還是挺滿意。
不知道如何擴大社交圈是現代人都面臨的尷尬問題,G rubw ithus顯然是期待用新科技讓人們相識,再用傳統社交方式使人們相知,可一個最關鍵的問題是那些害怕社交的人真的會從線上走到線下?萬一見光死怎么辦?萬一一起吃飯的人居心不良怎么辦?在芝加哥求學的中國人Jesscia雖然被G runw ithus 打著“real friends”的頁面說吸引,卻還未參加一個真實晚餐。
如果這樣的社交網絡來到中國,可能會有兩個明顯走向:約炮的人們來相聚或是大家一起來相親,當然也可以說后者是間接的約炮。現在的中國社交網絡現狀是和網友談人生容易,真實地碰面吃個飯卻沒那么簡單,假如G rubw ithus的用戶們大部分都是真誠的吃貨,也許現實接觸幾率會高得多吧,要知道吃貨也是世界上最單純可愛的生物。
3.遺愿都相同的人彼此會更有親切感?
Mylast wishes:發布遺愿的社交網站,把一群閑得蛋疼的人緊密聯系在一起。
會使用這個網站的人都是上輩子在一起,這輩子也必須在一起的命定朋友,首先它的作用如此之無聊,但還有如此這般的一群人認真對待。
遺愿都相同的兩個人,三觀一定不會相差太多,這樣的精神伴侶想必至少在線上會有個愉快的交流。也許他們的對話會如下:
“啊,我特別想在死前好好吃一回大蒜,不用擔心口臭!”
“對對!支持!棒呆了!我也是啊!一起!我要穿著大褲衩吃!”
然后在世界的某個角落會出現大啖大蒜的兩個人,他們詭異的愿望在彼此的鼓勵下都實現了,這可能才是m ylast wishes社交網絡的精髓:分享目前沒勇氣完成的愿望,在他人的鼓勵下努力去達成。這感覺就像做壞事一樣,一個人總覺得心慌慌沒底氣,一旦成眾就覺得沒什么了。
陌陌 “只愛陌生人”怎么就變得低俗了呢
陌陌是什么?隨時隨地認識周圍的陌生人
自從APP軟件下載開始普及后,人類似乎就進入交友饑渴癥的狀態,基于各種目的建立的社交族群軟件恨不得以每半周的速度進行升級和更新。陌陌就是自微信后,成為社交、交友界的下載之神,關于它還衍生出種種版本的神鬼志異和獵艷傳說。陌陌神奇之點在于它的移動社交功能,它基于地理位置進行社交。下載完軟件,就相當配有了一把開往世界之門的鑰匙。它神秘,你永遠都不清楚非主流照片后面究竟何人長何面孔;它隨意,你可以通過陌陌認識周圍任意范圍內的陌生人,查看對方的個人信息和位置,免費發送短信、語音和照片以及精準的地理位置,簡直就是弱化版的FBI偵探軟件。
類似于陌陌的還有Badoo,它也是基于地理位置的社交網站,它的最大優勢之一就是讓用戶直接操控自己的觀眾數量。越來越多人從陌陌轉向Badoo,不僅是因為陌陌有越來越低端和情色化的傾向,更重要的原因是,Badoo比陌陌更高級的地方在于其國際化,并且對于同志的容忍和接納度更高。
陌陌怎么了?成了帶有情色意味的“約炮神器”
網絡上關于陌陌有個著名的段子:“一對異地戀人每天在陌陌上聊天,彼此的距離始終都是1000km。情人節晚上她回家,習慣性打開陌陌,發現雙方的距離只有1km,再刷新,只有0.9km,她明白發生了什么,激動地走向門口……當晚,他們的距離只有-5cm。于是第二天,他們還是分手了。陌陌,發現愛的距離。”這當然是一個有內涵的段子,越來越多的網友和手機用戶把陌陌改稱為“約炮神器”,網友低俗化陌陌的原因在于,用戶幾乎以零成本或超低成本戀愛,一旦發現手機上出現100米以內的目標,就可以憑孤獨寂寞冷為借口,消解對方的戒心。更多年輕用戶則是把陌陌這類地理位置社交軟件當成調侃和談資的搞笑軟件,在深圳茶餐廳、仙蹤林和壽司店等常見到年輕學生圍成一團拿著手機調笑,深大一年級學生A m y說,她曾親耳聽到幾個男生評價距離他們0米的一名女生只是照片漂亮,人卻奇丑無比。同樣的還有Badoo,它的照片墻也有一定誤導性,很多人在見過0距離的真人后都大呼上當。
地理位置這類的社交軟件、網站似乎真的變味了。這樣未免有些傷害軟件和社交網站最初設計者的心。當別人口口聲聲說陌陌情色、淪為情色神器時,移動社交平臺陌陌創始人唐巖在回復媒體時稱,地理位置的社交意味著網絡交友與現實交友可以完全融合,最終成就一個移動端的社交王國,這個想法從來沒變過。或許,網友和手機用戶更該學會如何對這類地理社交軟件免疫,或者有預警被騙的方式,未來,也許還能出現專門針對這類社交網站真人頭像辨真假的軟件。
精確社交讓我們的生活變好了嗎?
今天的社交:庸眾的事業
城市頭條
按我的理解,人生在世,作為社會人與自然人,有三種社交方式,即與神(包括自然萬物)的交往、與自我的交往、與他人的交往。當然,這是一個廣義的、圓滿的、讓人成為人的社交概念。而今天我們談論社交的時候,基本上指的是后者,即與他人的交往,這是一個狹隘的、不圓滿的社交概念與意義指向。社交定義的狹隘化,促使它成為一種社會工具,而不是人的思想方式與智識景觀。也導致它成為貌似以信息交流為主旨的社會人群的一種扁平化的“事業”,我把這種意義失足了的社交,定義為“庸眾的事業”,它是現時代人的自我工具化、表征化與物質化的體現。
薩特說“他人即地獄”,在今天,與他人的社交,或許就是地獄式的社交,人們在地獄式的社交中,以各種電子表情,說著謊話,獲取感官刺激,娛樂與狂歡。娛樂化成為社交的主流傾向與目的。人們將社交精細化、明確化、細分化,其實是自覺與不自覺地,努力促使自己成為庸眾社會的一員。
在柏拉圖、蘇格拉底、孔子與諸子百家的時代,社交的概念還是圓滿的,那時候的人,不僅善于與神對話,與自然萬物交談,還與自我進行辯論,與他人的交流,基本上也是面對面的。那時候,社交即意味著目光與目光、聲音與聲音、精神與精神的交鋒與共融。社交就是一場感官的共舞與思想的華美宴席。社交的目的是更深入地認識自我、探索真知、探求真理。
那時代流傳至我頭腦里的社交印象是古希臘式的劇場里的辯論,從哲學家的思維洞穴中,我看見三條人所背負的西方神的咒符:欲望、知識、言辭。他們的社交場景,幾乎都圍繞著這三道咒符展開。先哲們試圖能以自身的智識,揭示與洞穿這些生命的謎團。
今天我們翻看柏拉圖的著作,幾乎都是“對話”,是思想式的社交的文本再現;孔子的《論語》,同樣是師生之間的社交景觀。“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孔子描繪了最本真的社交方式,三個人的組合,以“行”為軌跡,行是出發點,也是過程與目標本身,而讓“師”突顯出來,找到“師”,即是社交對境界的追尋。“師”作為真知的象征,即是各種社交的核心。沉思、傾聽、辯論———是古典式社交的“三段論”(三種方式、三個層面),也是讓社交成立的三個經典畫面。然而在今天,在電子時代的社交中,這三個畫面都已遠去。代之以聒噪、起哄、狂歡,這些特質,我們后面再詳細分析。我們先來看看近現代社交悲劇圖景。這一圖景,可以從尼采身上找到基本色調與主要線索。
在尼采的時代,人們的社交開始變得有缺陷,與神與自然萬物的交流少了。尼采說上帝死了。他的社交方式,基本是與自我的交往(但仍然具有沉思、傾聽、辯論的本質)。他發現了他那個時代的諸多“社交問題”,“人們忙于逐利,內心空虛,彼此厭倦得要命,因此不惜一切代價要‘把自己弄得有趣一些’,于是渾身上下撒滿了文化的作料,這樣就可以‘把自己當做誘人的美餐端上桌’了。”在尼采看來,社交就是一場假話的聯歡晚會。在《作為教育家的叔本華》一書中,他列舉叔本華杜絕社交式假話的行為,來贊美他的這樣一位悲觀于世界的導師,“他甚至不說那種討人喜歡的社交式假話,那是幾乎一切交往都有的,而且被作家們近乎無意識地模仿著的。”
尼采呼喚人“成為你自己”,“回歸簡單和誠實”。他反對、鄙視人像無頭蒼蠅一樣匆忙,或者陷在無所謂的虛偽的交往中。他說:“我們時代普遍的匆忙是文化整個被連根拔起的征兆,世界從來不曾如此世俗化。”
尼采說的怎么如此像當下的中國?
《查拉斯圖特拉如是說》,尼采用這樣一個超文本,總結了一個與自我社交的時代的“超人”精神,從他之后,社交就走向了狹義,走向了地獄式社交的今天。
如果說柏拉圖時代的社交展現的是“神義論”(宇宙論),那么尼采時代的社交圍繞的則是“人義論”(功利論),而當今時代的社交呈現的則是“物義論”(技術論),今天熱鬧的各類社交無不是建立在技術的革新上。以互聯網為載體的各類社交網站、社區、軟件,都是物化后的人的佐證,是“人是機器”這樣一個論斷的延伸。
面向全球的Facebook社交網站,據說有9億用戶,T w itter據說有2億;而在中國,新浪微博至2012年初,據說已超過2億注冊用戶,Q Q用戶據騰訊的官方數據是4億多。另外諸如被民間稱為“約炮神器”的陌陌、越來越普及的微信、人數上限50人的Path等等各類形態的電子社交服務器,也在迅猛地生長。今天的社交網絡,既有龐雜的交流平臺,也有以群落劃分的各類愛好小組。從宏觀到微觀,在技式之神的無微不至的服務下,它呈現出越來越明確、細微、精準的趨勢與服務線性。但縱觀電子時代的社交熱潮,無論是體量巨大的Facebook,還是小眾聚興的Path,都在訴說著一種“社交饑渴癥”。似乎人類陷入了一種空前的孤獨的恐慌,人類從未如此急切地盼望著與他人交流。地球人怎么啦?是都面臨著“喪父”與“喪子”之痛嗎?
蒙田在《論三種交往》一文中曾說:“生活是一種不均衡、不規則、形式多樣的運動。一味遷就自己,被自己的喜好牢牢束縛,到了不能偏離、不能扭轉的地步,這不是做自我的朋友,更不是做自我的主人,而是做自我的奴隸。”正如蒙田所說的,今天熱衷于各類社交的人其實是在做“自我的奴隸”,人們太熱愛技術,而成為“技術的奴隸”。
今天的人普遍已沒有沉思的習慣,淺思維與淺閱讀成為人的精神體征。人們如此熱衷于在一個虛擬的空間,通過電子的恒溫來表演自己,是因為他無法靜心來面對自己,來思考自身的存在,來想一想自己為什么活著,來梳理他與自然萬物的關系,來反思自己究竟該以何種方式與社會取得內在聯系。大多數人也喪失了聆聽自然與傾聽他人聲音的能力。今天我們時常會看到,一群人聚會,不是去聽他人說話,不是望著對方的眼睛,或就某個議題發表自身的觀點,展開辯論,去貼近他人的心靈,以確認他人與自我的關系,發現自我,而是各自拿著手機在刷微博。今天這樣的場景我們已司空見慣,習以為常。人們甚至喪失了聊天的能力。戲劇導演林弈華就曾談到自己觀察到的這類情況,一對年輕的情侶在一起,只是問問對方盤子里的東西好吃嗎?然后互相致以“還可以”,就沒了言語。年輕一代的言辭已退化,不如各類QQ表情那么豐富,這難道不是莫大的對人類自身追求技術精確的反諷嗎?
然而,人們通過社交是否又能找到真正的自己呢?答案自然也不容樂觀。在各類社交網站,比如微博上,我最直接的感受是這是一個彌漫著聒噪、起哄、狂歡氣息的話語場,當然微博在中國的狀況還比較特殊與復雜,它已不是一個簡單的社交概念。我們還可以國外的類似網站來談論,比如Facebook,很顯然,它抓住了“烏合之眾”的群體心理。然而它解決不了人們的孤獨,據說他的創辦者扎克伯格,在Facebook上就沒有一個真正的朋友。
當一個人自我心靈缺失,不能去直面自身時,社交只能讓他邁入更大的迷失。技術之神唯一鼓舞人們去做的事就是,做一個機器人。社交精細化、明確化、細分化,就是以它的功能性與功利性,勾引與誘惑那些自我意識缺乏的人成為越來越具體與逼真的機器的手臂。這也是快餐社會的一個需要,現代人恨不得能有人將食物嚼碎了送入他的嘴里,而發明一種食物可以滿足他最本能的欲望,他就可以不需要自己去體驗與思考食物的來歷。
其實這種看似多元的無限開放的社交平臺,它真正的作用是促使人走向單一與封閉。因為社交已異化成一種對自我欲望的滿足。這種以娛樂、以發泄、以本能的狂歡為指引的社交,它的群體特征自然也具有一種排它性。它激發的是一個庸眾社會的自我保護意識(或許在這里,我們也可以囫圇吞棗地套用麥克盧漢的說法,通過電子平臺,人又重新部落化了)。它與古典時代的社交的目的背道而馳,陷入其中的人,再不可能會像蘇格拉底那樣思考,那樣去觸摸與感知陽光;也再不可能,像尼采那樣去自省與反思,叔本華的孤獨與對真理的絕望。
尼采說:“一個人只要擁有真正的朋友,哪怕全世界都與他為敵,他也不會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孤獨。———唉,我的確發現,你們不知道什么是孤獨。”
在今天,社交的泛濫,或者也可以說是庸眾的“霸道”、技術所制造的強大的流行文化的狂歡。在這種環境下,不可能會有偉大的哲學家與思想家產生了。這也是我要定義今天的社交是“庸眾的事業”的理由。
當然,我不想以簡單的好與壞的言辭做出粗暴的評判,這一大多數人認為是自身福址的“事業”———這一技術的勝利。但我們可以去慢慢發現與確認這種以電子為載體的社交方式,對人的行為習慣與思維方式的改變,它是讓你變成你的主人,還是變成你被共謀了的“自己的奴隸”?







